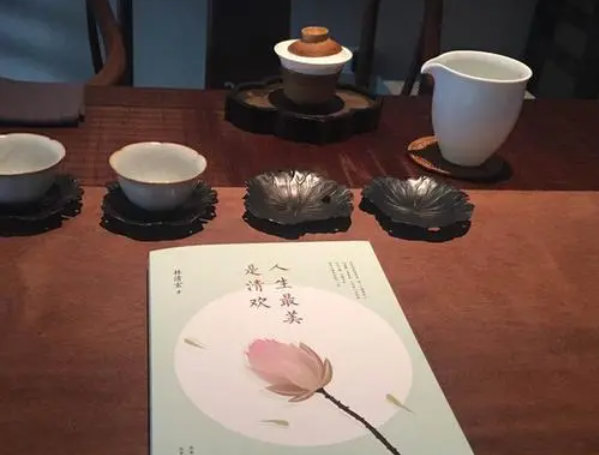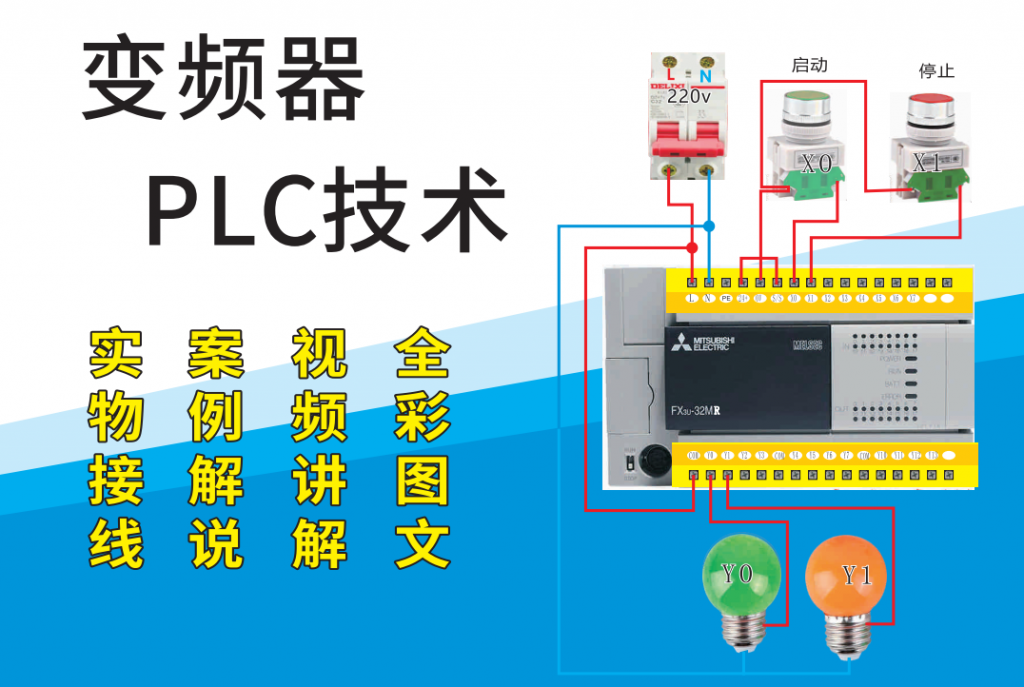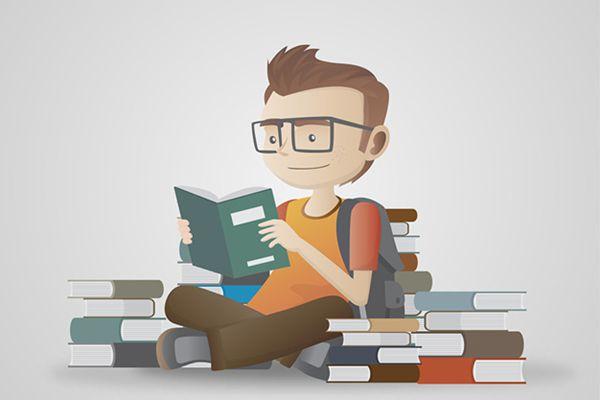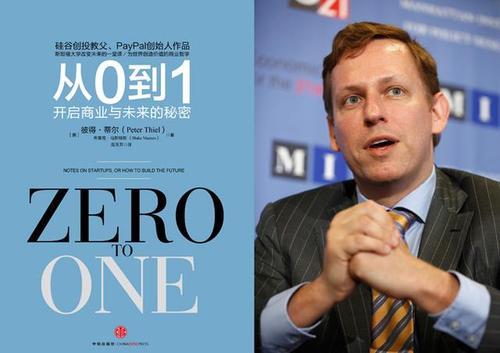我们一生最该坚持的习惯,就两个字“阅读”。阅读的分享主要是一方面自己做个笔记,另一方面也希望可以传播知识,跟大家共同成长,此文章为转载文章,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赫尔曼·黑塞曾说过:“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
它们似乎没有在你身上留下任何痕迹,但却深深地刻在你的灵魂、你的气质,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里。

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阅读之旅吧。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作品《今日简史》。
我们的生活正在与各种互联网科技公司高度融合,在享受各种数字化服务的同时,我们在这些平台上留下了清晰可见的痕迹,数据让我们毫无遮拦地暴露在虚拟世界中。
而当前有一个更加显著的趋势,那就是我们的数据越来越集中在极少部分的科技巨头公司手中——腾讯、阿里、谷歌、脸谱网等等。
这些公司无不掌握了庞大到无法估量的用户数据,并借此逐步构建起了数字霸权。
正如不久前,作为目前世界上最火爆的社交网站,脸谱网非法泄露700万名用户数据给一家名为Cambridge Analytica的政治咨询机构。
在听证会上,面对脸谱网涉嫌垄断的指控,CEO扎克伯格没有给出任何有效解释。
“用户离开平台后数据还会保存多久?”
“是不是得给你钱,才能保住我自己的信息?”
“脸谱网是否太过强大了?”
在各种暧昧模糊的回应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互联网巨头在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的霸权地位;作为个体使用者,我们在数字霸主面前太过弱小无力。
个人信息被储存在哪里?可能被谁拿去做了哪些分析处理?我们常常一头雾水,一无所知。

《未来简史》作者、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新作《今日简史》中讨论了当前数字霸权的问题。
尤瓦尔讲到,当掌控大数据算法的权利集中在一小群人受众时,我们面临着数字独裁的威胁。我们正在与算法绑定,被看透,被掌控。
数据在未来应该由谁掌握,目前我们对此的关注和讨论还远远不够。

我们尚未意识到数据的真正价值
很多人一直没有弄清楚数字霸权是如何出现的;为何数据在这批强大的科技公司手中,能转化为难以置信的财富和统摄力。
首先,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数据的价值。
在这个数字时代,数据的价值就好比农耕和工业时代的土地和机械,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
在古代,土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资产,一旦太多的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就分裂成贵族和平民。
到了现代,机器和工厂的重要性超过土地,各种利益集团转为争夺这些重要生产工具的控制权。
等到太多机器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就分裂成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但到21世纪,数据的重要性又超越土地和机器,于是新的斗争就是要争夺数据流的控制权。
等到大多数据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部分群体将一跃成为新的“统治阶层”,成为世界的新霸主。

当下人类可能已经完全和计算机融合,一旦与网络断开便无法生存。在接入数字设备的过程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被监控,被记录,被分析。
这些数字巨头完全可以通过算法摸清你的脑子在想什么,甚至更进一步与你的意识同步,预测并干涉你的思维和选择。

我们已经沦为数据巨头的商品
数据和算法的威力超乎人的想象。争夺数据的比赛已经开始,目前是以谷歌、脸谱网、百度和腾讯等数据巨头为首。
到目前为止,这些巨头多半采用“注意力商人”(attention merchant)的商业模式:靠提供免费信息、服务和娱乐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再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卖给广告主。
然而,这些数据巨头掌握的数据远比任何广告收入更有价值。我们不是他们的顾客,而是产品。
DeepTech深科技曾经发布过一篇报道,讲述为何像苹果、微软这样的互联网科技公司能保持绝对领先的地位,原因就在于它们通过对用户数据进行分析,不断巩固提升自己的在行业内的霸主地位。
“这些数据的详尽程度是过去其他公司难以想象的,它们可以帮助巨头公司提升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反过来又为它们增添了新的用户,获得更多数据——又是一个良性循环。谷歌通过用户点击习惯,不断地改进搜索结果和广告服务。

亚马逊、Netflix和苹果通过挖掘用户数据来优化个性推荐算法,让自己提供的产品对用户更具吸引力。”
举个例子,也许你很久前看过一部片子,早就忘记了大半情节,但你的观看数据会被Netflix、亚马逊或任何拥有这套电视算法的人记录并分析,它们将会知道你的性格类型,也知道怎样能触动你的情绪。
有了这些数据,Netflix、亚马逊会帮我们挑片挑得精准无比。你对这些完全一无所知,但算法对这一切却了如指掌,而且这些信息可以卖几十亿美元。

该由谁拥有数据?
越来越多的数据从我们的大脑和意识,流向企业和政府的数据接收器,而一般人会发现很难抗拒这种过程。
至少在目前,人们都还很乐于放弃自己最宝贵的资产(他们的个人信息),以换取免费的电子邮件服务和可爱的猫咪影片。
这有点儿像非洲和美洲的原住民部落,不经意间就把整个国家卖给了欧洲某国,换来各种颜色的珠子和廉价饰品。
如果大众未来想要阻止数据外流,可能会发现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几乎所有决定都得依赖网络,甚至医疗保健和生命延续也不例外。
如果我们想要阻止一小群精英分子垄断这种神一般的权力,关键的问题就是:该由谁拥有数据?
关于我的DNA、我的大脑和我的生命,这些数据到底是属于我、属于政府、属于企业,还是属于全体人类?
授权让政府把这些数据国有化,或许能够对大企业发挥抑制作用,但也可能导致更多的舆论管控。而把数据交给如脸谱网的扎克伯格,可能最终又会转手变卖给第三方公司。
“把数据所有权握在自己手上”听起来更有吸引力。当前,我们普遍的经验通过各种网站和服务商的授权协议,允许这些组织收集使用我们的信息。
比如注册淘宝时,我们被要求同意《淘宝平台服务协议》及补充协议《法律声明及隐私权政策》。

但实际上许多用户对数据授权协议只是一扫而过,甚至忽略《服务协议》或《隐私声明》的具体内容,并不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可能被共享或转卖。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用手机安装、打开第三方应用程序时,仅28.9%的受访者会仔细查看授权列表,52.4%的受访者会大概看一眼,17.1%的受访者基本不看。
而即使认真查看细则的人,后续也极少追踪组织对自己数据的使用情况。
这反映出我们对保护个人数据严重缺乏经验,从思想意识到技术操作还远远没有跟上现实的要求。
讲到要拥有土地,我们已经有几千年的经验,知道怎么在边界上筑起围篱、在大门口设置警卫、控制人员进出。
讲到要拥有企业,我们在过去两个世纪发展出一套先进的规范方式,可以通过股票的买卖,拥有通用汽车和丰田汽车的一部分。但讲到要拥有数据,我们就没有太多经验了。
这是一项更为艰难的任务,因为不像土地或机器,数据无所不在但又不具真实形态,可以光速移动,还能随意创造出无穷无尽的副本。
举例来说,能不能用算法形成网络,支持全球人类社群,让所有人共同拥有所有数据,一同监督未来的生活发展?这种建议是否可行?
尤瓦尔在《今日简史》断言,数据的所有权问题,将是整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他呼吁所有政治家、企业、科学家、律师,甚至哲学家,加快脚步,共同研究解决方案。

你为什么会失业?
失业的威胁不仅来自兴起的信息技术,更来自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融合
人类有两种能力: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过去,机器主要是在原始的身体能力方面与人类竞争,而人类则在认知能力方面享有巨大优势。
因此,随着农业和工业迈向自动化,就出现了新的服务业工作。这些新工作需要人类拥有独特的认知技能,包括学习、分析、沟通等,特别是必须理解人类的种种情绪。
而今天,人工智能已经在越来越多的认知技能上超越人类,包括理解人类的情绪。而且,除了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之外,我们并不知道还有什么第三种能力可以让人类永远胜过机器。
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一个关键点是,人工智能革命不只是让计算机更聪明、运算得更快,还在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有诸多突破。
在过去几十年中,在神经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让科学家能够“破解”人类,更清楚地了解人类究竟是如何做出各种决定的。
事实证明,我们从选择食物到选择伴侣,都不是出于什么神秘难解的自由意志,而是数十亿神经元在瞬间计算各种可能性的结果。
过去大受赞誉的“人类直觉”,其实只是“辨识模式”罢了。
这意味着,就算是那些原本认为依靠直觉的工作,人工智能也能表现得比人类更好。

人工智能不会比人类更有那种难以言喻的第六感,但人工智能比人类更懂得计算概率和模式识别。
不管是司机预判行人想往哪儿走,银行经理评估借款人的信用好坏,还是律师衡量谈判桌上的气氛,依赖的都不是巫术,而是在他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大脑就会通过分析面部表情、声调、手部动作甚至体味来识别生化模式。
人工智能只要搭配适当的传感器,绝对可以把这些工作做得比人类更精确、更可靠。
因此,失业的威胁不只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兴起,还因为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融合。脑科学家今天对杏仁核和小脑的研究,就有可能让计算机在2050 年比人类更适合担任精神病学家和保镖。

人工智能的两种“非人”能力
人工智能不仅能够侵入或破解人类,在以往认为专属于人类的技能上打败人类,更拥有独特的非人类能力,使得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的差异不是程度高低的问题,而是完完全全的两回事。
人工智能特别重要的两种非人类能力是“连接性”和“可更新性”。
人类都是个体,很难将所有人彼此连接,从而确保他们都能得到最新信息。相反,计算机并不是彼此相异的独立个体,因此很容易把计算机集成为一个单一、灵活的网络。
所以这样说来,我们面临的不是几百万台计算机和机器人取代几百万个工人,而是所有作为个体的工人都会被一套集成的网络所取代。
因此,讨论自动化的时候,不该把“一位司机”的能力拿来和“一台自动驾驶汽车”比较,也不该把“一位医生” 和“一位人工智能医生”进行比较,而该拿“一群人”的能力和“一套集成网络”进行比较。
举例来说,如果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出现某种新的疾病,或者某实验室研制出某种新药,目前几乎不可能让全世界所有人类医生都得知相关的最新消息。
但相较之下,就算未来全球有100 亿个人工智能医生,各自照顾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仍然可以在瞬间实现全部更新,而且所有人工智能医生都能互相分享对新病或新药的感受。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把个体人类转换为计算机运算网络之后,就会失去个性化所带来的优势。
他们认为,如果某位人类医生做出了错误判断,并不会因此让世界上所有的患者都丧命,也不会阻碍所有新药的发展。

相反,人工智能医生都属于某一系统,一旦该系统出错,结果可能就极其严重。
但事实上,集成的计算机系统可以在不失去个性化优势的情况下,把连接性的优点发挥到极致。
比如可以在同一个网络上运行多种算法,这样位于偏远丛林山村里的病人通过智能手机能找到的就不只是某位医学权威,而是上百位不同的人工智能医生,而且这些人工智能医生的表现还会不断被比较。
你不喜欢那位IBM 医生的诊断吗?没关系。就算你现在被困在乞力马扎罗山上,也能轻松找到别的医生,寻求第二意见。
这很可能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好处。人工智能医生能为几十亿人带来更好、更便宜的医疗保健服务,特别是那些目前根本没有医疗保健服务可用的人。
因此,如果只是为了保住工作就拒绝相关领域的自动化,绝对是不明智之举。毕竟,我们真正该保护的是人类,而不是工作。
显然,目前还没人能够确定机器学习和自动化究竟会对未来的各种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想预估相关时间表也绝非易事。
但我们不能太过乐观,一心认为会有足够的新工作来弥补被淘汰的工作,将会十分危险。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在21 世纪给人类带来的挑战,会比蒸汽机、铁路和电力在上个时代带来的挑战大得多。
现代如果测试失败,可能导致的就是核战争、基因工程怪物或生物圈的彻底崩溃。所以,我们只能比面对工业革命时做得更好才行。

人工智能究竟会不会有意识?
人类之所以能够控制世界,是因为合作的能力高于任何其他动物,而之所以有那么强的合作能力,是因为他们能够相信虚构的故事。这样说来,剧作家的重要性绝对不在士兵之下。
现今,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人非常多,而去读关于机器学习或基因工程文章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会去看《黑客帝国》、《她》之类的电影,以及《西部世界》、《黑镜》之类的电视剧。
正是这些影视作品,塑造了人们对于现今科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认识。这也意味着,科幻小说在描述科学现实的时候必须更负责,否则就可能让人产生错误的想法,或是把注意力浪费在错误的问题上。
我们知道,几乎所有关于人工智能的电影和小说,基本情节都围绕着计算机或机器人产生意识的那个神奇时刻。而一旦它们有了意识,不是人类主角爱上机器人,就是机器人打算杀光所有人类,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因此,我们常常过度担心在未来的某一天,感情充沛的机器人与人类之间发生点什么,这就是现代科幻小说最糟糕的问题——混淆了“智能”和“意识”的概念,并认为如果要有与人类相当甚至更高的智能,计算机就必须发展出意识。

事实上,至少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不用担心科幻小说里那种人工智能产生意识、杀光或奴役人类的噩梦。我们会越来越依赖算法为我们做决定,但算法不太可能有意识地操纵人类。
真要思考人工智能的未来,我们该担心的,是有一小群超人类精英凭借算法带来的力量,与大量底层的退化智人之间发生冲突。比较值得参考的仍然是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而不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
大脑仍是人类认知的“黑洞”
我们暂时不相信人工智能会获得意识,是因为智能和意识是天差地别的两种概念。智能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意识则是能够感受痛苦、喜悦、爱和愤怒等事物的能力。
我们之所以会两者不分,是因为对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来说,智能与意识会携手同行。哺乳动物处理大多数问题时靠的是“感觉”,但计算机会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提高智能的路其实有好几条,其中只有一条需要靠意识。就像飞机不用发展出羽毛,但飞行速度却比鸟更快,计算机也不用发展出哺乳动物所需要的感受,就能比哺乳动物更会解决问题。
确实,人工智能必须准确分析人类的感受,才能好好替人类治病、找出人类的恐怖分子、为人类推荐另一半、在满是行人的街道上行车,但是这一切并不需要它自己有任何感觉。
算法只需要学会辨别猿类在快乐、愤怒或恐惧下的生化模式,而不需要它自己感受到快乐、愤怒或恐惧。
当然,人工智能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发展出感受。我们目前对意识的了解还不足以完全下定论,时至今日,大脑依旧是人类认知的黑洞。
科学家正在尝试类人脑神经网络模型和计算方法的建立以及类脑计算、处理以及存储设备技术的研究,尽管霍金、比尔·盖茨以及马克斯等业内知名人士忧虑人工智能的发展,但是这没能阻止类脑科学如火如荼地发展。

然而,就目前人类具有的知识来看大致而言,需要考虑三种可能:
1. 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与有机生化相关。因此只要是非有机体的系统,就不可能创造出意识。
2. 意识与有机生化无关,而与智能有关。这样一来,计算机就能够发展出意识,而且如果计算机要跨过某种智能门槛,就必须发展出意识。
3. 意识与有机生化或高智能并无重要关联。这样一来,计算机确实可能发展出意识,但并非绝对。计算机有可能具备极高的智能,但同时仍然完全不具有意识。
这些可能都无法排除,正因为我们对意识所知太少,短时间内并不可能设计出有意识的计算机。因此,虽然人工智能具有巨大的力量,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以人类的意识为准。

退化的人类滥用进化的机器
现在的危险在于,如果我们太注重发展人工智能而又太不注意发展人类的意识,那么计算机有了极先进的人工智能之后,可能只会增强人类的“自然愚蠢”。
在未来几十年内,我们虽然不用解决机器叛乱的问题,但机器人可能会比你的父母更知道怎样触动你的情绪,并且会运用这种神奇的能力来对你进行推销,让你买某辆车、把选票投给某个人,或是接受某种意识形态都轻而易举。
这些机器人能够找出我们最深层的恐惧、仇恨和渴望,再用它们来对付我们。
从最近全球的选举和公投就可以预见未来:黑客通过分析选民数据,运用选民现有的偏见,就能知道怎样操纵单个选民。
科幻惊悚片常常上演的是烈火浓烟、轰轰烈烈的末日景象,但实际上,末日景象可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点击当中悄悄而且平凡地来临。
想避免这种结果,每投入一美元、一分钟来提升人工智能,就应该同样投入一美元、一分钟来提升人类意识。

但很遗憾,目前对于人类意识的研究和开发并不多。我们对于人类能力的研发,主要都是为了满足目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迫切需求,而不是为了让人类保有意识。
上司希望我们回复电子邮件越快越好,但他对于我品尝和欣赏食物的能力毫无兴趣。结果就是我连吃饭的时候都在收电子邮件,也就慢慢失去了重视自己感官感受的能力,沦为机械的劳动者。
就像我们会投入大量心力想了解证券交易的种种奥秘,但几乎不花什么心思来了解痛苦背后有什么深层成因。
至此,人类就像是其他经过驯化的家畜。例如我们培育的奶牛,性情温顺,乳量惊人,但在其他方面远远不及其野生祖先,没那么灵活,没那么好奇,也没那么懂得变通。
我们现在也正在培育一种驯化的人类,产生的数据量惊人,而且能够像海量数据处理装置中的高效芯片一样运转,然而这些“数据牛”绝对称不上是发挥了人类的最大潜能。
事实上,我们还太不了解人类的心智,根本无从得知人类的最大潜能是什么模样。然而,我们几乎没有投入什么心力来探索人类的心智,只一心想着提升网络连接的速度及大数据算法的效率。
如果再不注意,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进化,人类就会越来越愚蠢,最后的局面就会是退化的人类滥用进化的计算机,伤害自己,也伤害世界。
正因为一部分人类可能会被“驯养”,也就有可能创造出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让所有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大多数人类的痛苦将不再是受到剥削,而是更糟的局面:再也无足轻重。